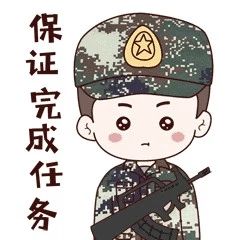1
早晨5点半,屋檐下鸟窝里会有叫声,这是麻雀出去捕食的讯号。米墨风把闹钟定在6点钟,可每天5点半,她便醒了。不过她并不会睁开眼睛。
换一个平躺的姿势,静静地躺在床上,当第一声鸟鸣过后,她感到了新的一天的一丝阳光似乎透过窗帘,透过被子洒在身体上。她想去收集这些光,慢慢从脖颈开始抚摸过锁骨、肩膀、先是左边的胸部、然后是右边、胃部、腹部、肚脐、胯骨、稍有一些毛发透过皮肤长了出来,颗粒般的触感,接着是阴道。
所有的这一切完毕之后,平复呼吸,6点的铃声响起,起身喝一杯白开水,洗澡,用黑色的毛巾和无任何香料的肥皂,连同头发一起洗干净。对着镜子认真检查,如果看到长出来的毛发,就用剃刀一点点剃掉。
早餐是两片面包,一个白煮鸡蛋。
7点出门,步行上班,到公司正好是7点50分,距离正式的上班时间还有10分钟,来得及换上工作服和鞋子。
中午一般会选择素食,在员工食堂吃最简单的食物,一碗菜,一碗饭。
要把饥饿感全部留到晚上。虽然营养专家曾经说过,一日三餐的黄金法则是早晨大于中午大于晚上,但是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一天当中的前两顿只能是对于保持体力和脑力的一种营养补给,充满了敷衍的味道。只有在下班之后的那顿晚餐,才是真正对于自我的满足。当然也有很多人对于晚餐仍旧是草草了事。米墨风不想这样虚度一生,她决定在晚餐当中好好犒赏自己的胃,而要激发对于食物的兴趣和热情必须保持一定的饥饿感和匮乏感。
下午4点公司下班,步行到超市购买火腿、蘑菇、绿豆、番茄、牛肉、豆腐等想要品尝的食物,回到家进行加工。搭配的主食永远都是一碗白米饭。营养学家说的多吃粗粮少吃白米的理念不能接受,世界上最好吃的主食当然是白米饭,如果为了多活几年而要改吃那些粗陋的糙米、麦麸,忍受几十年难过的口感,那么多活几年又有什么意义呢?况且吃白米饭快30年,米墨风还没发觉身体上有任何不适。
家里用来喝啤酒的玻璃杯,小半杯米可以做出一碗白米饭,恰好够自己一顿晚饭。这是多年的单身生活积累出来的经验,多一点则多,少一点则少。一般来说,她会把烹调的晚餐全部吃光,很少会出现做多了的情况。偶尔剩下一点点,会全部倒掉。
吃过饭的时间一般是晚上7点半。8点钟,米墨风踏上跑步机跑步,播放一部电影。
一般来说都是老掉牙的片子,固定看的大概是《罗马假日》《廊桥遗梦》《这个杀手不太冷》,国产片只看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从来不看电视剧,不看任何综艺节目和新闻。这对于她来说是浪费时间的事情,并且是一种干扰。她固定用自己的看法来看世界,用自己的习惯来生活已经坚持了几十年,皮肤紧绷,脸色康健,自给自足,没有任何缺憾,也没有任何节外生枝的惊喜。这对于她来说,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生活,也不是什么差劲的生活。她有几个不经常联络的朋友,大概保持在每年联络一两次的频率,不煲电话粥,只见面。面对朋友的提问,她数年来都是这样回答的:还是那个样子啊,挺好的。
每天健身过后她会看书到深夜,无聊的时候她听听mp3,里面收录了张国荣的大部分歌曲。
睡觉的时间一般在晚上12点以后,她似乎不需要8小时的睡眠,从小到大,只要四五个小时就足够了。
2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她一成不变的日常还是发生了稍稍的改变。
八个月以前,厨房的水管出现问题,物业没能修好,她自己当然不能胜任,于是给维修公司打电话,前来维修水管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年纪看上去应该比她大了至少十岁。脸上已经出现一道一道的皱纹,不过那皱纹看起来很干净,沟壑里面不像是有灰尘的样子。男人进门前礼貌地穿上了鞋套,米墨风注意到他穿着洗得已经发白的旧牛仔裤,深蓝色的鸡心领毛衣,里面是一件灰格子衬衫,衬衫最顶端的扣子没有扣上,呈倒三角形打开在脖颈两遍,衬衣的领子还算挺立,露出来的那块倒三角形状的脖子上面略有松弛连着光洁的下巴和一张偏白的脸。
他戴着黑框眼镜,鼻毛一定经过了仔细修剪,耳窝也经过了一定的清洗,里面基本没有皮屑,头发剪得很短,但又不夸张。
“水管有沙眼,不能用堵的方法,还是换一根吧。”
他的声音意外地很年轻,浑厚有力,清亮没有沙哑的杂音,他的牙齿干净洁白,他应该不吸烟。
“你可以自己去买,我告诉你型号,等你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我再过来。或者你信得过我的话,我去给你买回来,今天就能换上。”
米墨风选择了后者。
维修工回来的时候,米墨风给他倒好了热热的红茶。他摆摆手:“谢谢,不用了,我带了矿泉水。”
他是一个有分寸的人,不轻易使用别人的杯子,陌生人使用过的杯子,主人可能需要在陌生人走后仔细刷洗,他大概顾虑到了这点,这是很难得的礼节。
他告诉她,水管安好之后应该不会再有问题。这栋房子年头太久远,以后恐怕其他水管还会坏,他教她用手纸擦拭水管的方法,可以准确找到漏点。
她连连说谢谢,付了钱。
他也说谢谢,之后离开。
两个月后的深夜,她刚刚上床,便听到家里滴答滴答的声音,厕所里的水管不断滴下水来,她突然想起了那位维修工,果然如他所说,房子老旧严重,水管陆续都出现了问题。夜间不能打电话找人维修,她蹲在地上接了一夜的水,不敢睡也不敢离开。
可能是夜里着了凉,第二天她就发烧了。
水管不能不修,她又打电话到先前的维修公司。经过一番交涉,没过多久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又是他。手里拎着一根崭新的管子。
“真叫我说中了,又坏了。”他麻利地戴上鞋套,进了屋。看见她站在屋子中间摇摇晃晃,没走几步就往下倒,他拿着水管的那只手擎住了她的身体。
恍惚中她看见一个人站在她的对面,还是灰色格子的衬衣,不过这次灰色格子上多了几条红色的花纹,毛衣这次是浅蓝色,还是那条旧旧的牛仔裤。黑框眼镜里,一双眼睛一直看着她。
“你终于醒了,烧得很厉害,你家里人呢?要不要给他们打电话?”
她摇摇头,掀开被子下床。
“要不我送你去医院?”
她摇摇头往厕所走,艰难地蹲下来看新换上的水管,用手摸了摸,不漏了。
“你家里有药吗?要不我帮你买一点送上来?”
她摇摇头。
他突然局促起来,环顾四周,看了看这个简单到连一个毛绒玩具和棉布靠垫都没有的房子,顿了口气,“你烧得挺厉害,好好养着吧,我走了。”
她说:“等一下。”
他反应过来:“哦,对,钱还没给。”
她说:“你可不可以陪我呆一会儿。”
她也不知道口中怎么会说出这几个字,原本她是打算说“钱在桌子上,你自己拿吧”,原本她是想说“谢谢你,慢走”的。但是她却说了要他陪一陪。她一定是烧糊涂了,又或者感冒发烧攻破了她坚硬的外壳,终于她可以有一个瞬间承认自己其实很孤单。
3
他把她抱在胸前,她的背部靠着他的胸膛,他们的腿像某种昆虫一样呈向外弯曲的状态交叠在一起,她的臀部紧贴他的下腹,他们偶尔会聊几句,更多的只是这样躺着,有时候他会猛烈地撞击她的后背、尾骨,不过她更喜欢他放慢速度,一点一点的让她感受到皮肤之间的摩擦。
他们像两只侧立的勺子一样,勺子把贴着勺子把,勺子肚贴着勺子肚,贴合在一起。
每周日的中午,他会来到米墨风家,彼此没有太多的寒暄,只是躺在床上做爱。虽然首次他曾提出过疑问,但米墨风以清醒的头脑和富有逻辑的一句话打破了他的所有顾虑。“我只是需要一具身体而已,你不必担心我会给你带来麻烦,我不会问你的名字,有关于你的现状,你的家庭或者你的生存法则,我只是需要一个温热的男人的身体。同样你也不必问我,如果我很唐突的话,那么我很抱歉,请你离开,如果恰好你也需要的话,那我们就开始吧。”
他原本以为她只是一个饥渴过度的单身女青年,然而她只是静静地抚摸过他的每一寸皮肤,并没有过分夸张的情欲,更多时候,他们不过是赤裸着相互拥抱在一起,静静地躺在床上,如同两具扭缠的尸体。
床单是白色的,窗帘也是,墙角有一棵绿植,有时候他嗅着她丝毫没有任何香气的头发,看着那棵突兀的绿植。
他还是不太习惯用她的杯子喝水,每次都带一瓶矿泉水。
他们大概只会躺在一起两个小时,然后各自说再见。
关上了门,各自走开。
米墨风曾在一个早晨起来对着镜子检查,毛发没有变多,体型也没有丝毫变化,体重没有变重也没有变轻,脂肪率、骨含量没有变化,心率也还是老样子。每一天过的还是那样的节奏,不快也不慢,周日在周六之后到来,唯一的改变是,周日的中午她坐在家里,不必穿正式的服装,只需要一件对襟的睡裙就可以了。因为过不了多长时间,门铃响了之后,这件睡裙就会脱下来。
4
第26个周日过完之后,他再也没有来。
第27个周日,她像往常一样穿着对襟的白色睡裙坐在沙发上看书,不知看了多久,门铃一直没有响,窗外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她才意识到已经是傍晚了。
她并没有在意他的爽约,原本他们也没有定制什么不可打破的计划。他们从来没有定规,没有关联,没有答不答应,也没有任何承诺。
或许他临时有事。
但是接下来的第28个周日,他也没有来。
第29个周日也没来。
她确定他不会来了。
或许之前不曾想过的事情,不曾考虑过的危险他又开始重新考虑,或许他也是一个大龄未婚男性,即将和未婚妻结婚,现在已经步入婚姻殿堂,无法再与另外一个陌生女人保持这样的关系。或许他突然觉得受到了某种道德方面的束缚开始害怕这种约会。说到底她并没有做什么影响安定团结的事,可这种事终归不能大大方方说出去。他总不能一面喝着酒一面跟哥们说:“最近我每周日都和我的一个女顾客上床。”这实在是说不出口的。
可能因为这种种,他不再来了。
本来就没有期待,何来失望。本来就没有约定,何来爽约。
只是少了一具身体,一切照旧。
她的日子照样过着,和以前没有任何不同。只是在最近,她总是把菜做少了,要嘛就是把菜做多了,有一次剩下了半盘,还有一次,当想要夹牛肉片卷金针菇的时候去发现已经没有了,可米饭还剩下半碗。突然难以把握的厨房让她多少有一点点烦躁。
她开始失眠。
虽然她习惯晚睡,可从不失眠。但最近一段时间她开始失眠。其实也没有想什么,脑子里还是空空的,只是会突然有一些线条,一些片段,她认为自己并没有故意去想什么,为什么一些琐碎的片段会掉落出来?
这样让她烦恼。
今夜她又无法入眠,索性开了灯,双手抱头,躺在床上打算不再跟自己的脑袋做对,既然那些片段掉出来,不如就好好回忆一番。
她喝了一口水,如同准备好了要上战场的架势一样,开始要回忆往事,脑海里浮现出的竟然是他温热的身体,那一双因为干活儿有一点点粗糙的手,触摸在皮肤上有些许粗粝的感觉,然而他的臂膀结实,枕在上面能感受到被涌动的血液包围着。
她想起他们唯一可以算做谈话的一次谈话,他问她:“你为什么拒绝男人?”
她笑:“我明明和你睡过,你怎么说我拒绝男人?”
他说:“因为你做爱的时候像一条离开水的鱼。”
她说,小学的时候每周三下午放假,她的父母太忙,没办法接她。每周三的下午她都和几个同样没有父母接的同学留在班级里写作业,等待傍晚下了班的父母来接。那天教室里来了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他是班主任老师的儿子,他经常来学校玩,很多同学都认识他。那一天很奇怪,原本和她在一起的同学突然都不见了。他反锁了教室的门。
“你后来没有告诉父母?”
“没有。”
“为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描述,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我只是觉得很恶心,很讨厌。并且我的父母那时全部的目光都在我的弟弟身上,我想,即使我说了他们也不会在意的,我并不知道那件事的本质,我以为那不过是男孩子的恶作剧。后来等我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我正在谈第一次恋爱,然后我失败了,我突然觉得非常恶心,恶心透了,我没办法接受他提出的要求。他和我分手了,他觉得我是一个奇怪的女孩。”
“如果我再年轻几年,我一定会娶你的,不过我想我没有资格。”
“你没必要同情我,我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你,如果我认识你,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
“那你为什么……”
“你可以理解成我孤单,也可以理解成我很恶心,还可以理解成我很好奇,有某种打破传统的受虐倾向,或者干脆把我当成怪物什么的,好吗?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不是吗?我是我,你是你。就这样。”
“不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你可以说,但我一定不问。”
“真是个奇怪的女孩,好吧,我呢,原本有一个很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很顽皮的儿子,住着一栋不大不小的房子,上着千篇一律的班,我觉得生活挺带劲的,我想多挣一点钱让孩子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我以为我一直很努力,我的妻子一直很爱我,可是有一天她跟我说离婚吧。因为她已经预料到了,这辈子跟着我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大概会永远住着这栋房子,永远只能去便宜的饭店,永远买不了昂贵的包包,永远坐不上宝马或者奔驰。”
“所以你同意了?”
“嗯,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我可能一无是处,但这点风度还是应该要有的,当一个女人不愿意和你一起过的时候,你不需要其他理由了,这本身就是理由。”
她点点头,“你果然很绅士。”
“孩子喜欢跟着她,所以我把房子和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她,于是我一夜之间就成了没有家的流浪汉,目前住在公司的仓库里。以前我很努力的工作是为了让儿子能够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现在我拼命干活是为了自己,不然我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横尸街头,连收殓自己的棺材钱都没有。”
“哦,你不必害怕,我不会要求住在你这里的,我这几个月的工作都不错,已经拿到了奖金,下个月我就可以租房子了。”一段沉默之后,他突然说。
“你真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他吻住了她的嘴唇,不让她再说话。他们见面已经很多次,从第一次开始便是赤裸裸的上床做爱,却从来没有吻过。那是他第一次吻她的唇,也是他们第一次激烈的做爱。
那天快到傍晚了,他才离开,临走前还吻过她的额头。
她的脸一直是通红发烫的,直到半夜都没有消退,不知道为什么她并不反感他这样做,她第一次走到窗前看他离开的背影,并不匆忙,稳定的步伐,渐渐消失。
那天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她突然有一点点后悔,没有问过他的名字,也没有告诉他自己的名字。
他只是在接维修单子的时候知道她姓米。
她突然想起来什么,开始翻找自己的手机,第一次维修水管的时候他曾打电话来确定她家的方位。她有清理电话通讯录的习惯,从来不会为了任何人保留电话号码,并且从不轻易留下自己的电话。她知道那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早在当天他修理水管离开之后,就被她抹去了。可还是徒劳地把手机翻了一遍。而他,一直没有给她打过电话。
她笑自己犯傻,她曾说过她和他是无关的两具身体而已,谁也不需要谁,谁也不欠着谁,谁也用不着谁。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要给自己打电话呢?
她用理智稳固自己的心,梦境却一次一次暴露弱点。
她开始想念他了。
然而他在梦里,总是一具没有头颅的尸体,丝毫没有温热,像锁扣一样自我纠缠,怎么也掰不开解不开,那具尸体从不拥抱她,更不会吻她。
她已经好几个夜晚被这样的梦吓醒。
她打开电影,不知道是第几百次看《这个杀手不太冷》,看到娜塔莉波特曼把绿植种在园子里的时候,她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跑到卧室的墙角。那棵绿植一直默默待在那里,它是这栋房子里除了她唯一的活物,是唯一一个见证了她与他纠缠的每一个瞬间的生命体。此刻她很想找一个很了解她的生命体对话,然而绿植并不会说话,连哼一声都不会。
她哭了,眼泪滴在叶子上,顺着叶片滑进了植株的根儿。
第二天,几片叶子烂了,即将凋零。她记得刚刚搬来的时候买了这株沙漠植物,完全是因为它几乎不需要浇水,她对于一切需要照顾需要关照的东西都感到恐惧。几年来,她与它相安无事,互不干涉,彼此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她从未好好看过它,从未浇灌它,而它也一样寡淡,连她的一滴眼泪都难以承受。
她终于受不了这种无边无际的折磨,鼓足了勇气打电话到维修公司。
“你好,我是兰花小区9号楼的米女士,先前曾给你们打过两次电话维修水管,请问给我维修水管的工人还在吗?”
“哦,女士你好,你的水管没有修好吗?我们可以派别的工人去一趟。”
“哦,不是,呃,我只是想找他。”
隔了几分钟,电话那边终于传来了回音。“我查了一下,两次给你修水管的都是维修工刘杉,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他不干了?”
“不,他不在了。唉,您没看新闻吗?刘杉两天前为了救一个横穿马路的小男孩,出事了。”
“……哦。不好意思,麻烦你了,再见。”
两天以后,米墨风找到了事发之后的晚报,头版大大的标题写着《家政维修工人车轮下救男童,广场上千余人为他点蜡祈福》。
那一晚,米墨风又做了梦,梦里成片的杉树,漫山遍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