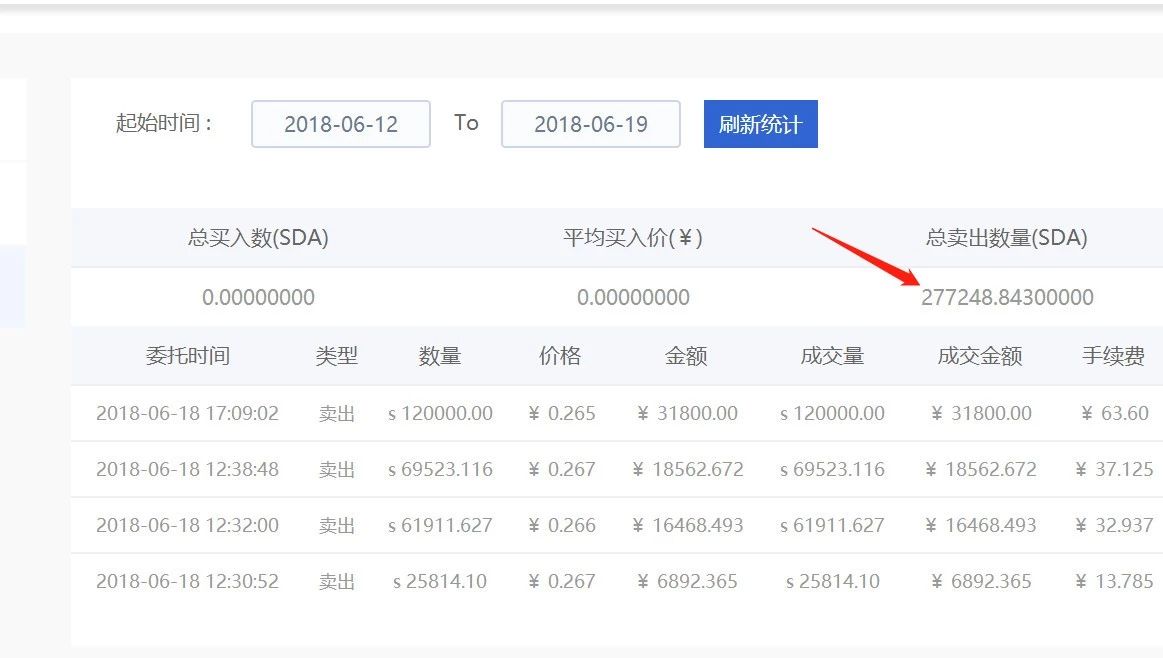(一)
到家时是下午四点左右,一般这个时间点父母都在工地上,可没想到大门居然是敞开的,走进堂屋听到有声响,一看父母的卧室,有人在看电视,我喊了一声,“妈,是你啵?”那人一回头,却是碧珠娘。她一起身,瓜子壳从她衣服前摆上沙沙落地,“你么回了嘞?”我说:“到武汉出差,正好从屋里过一趟。”说着话,我进了卧室,原来只有她一个人,“我妈嘞?”她又坐回沙发上,从玻璃桌上拿起瓜子继续嗑,“你妈还在建华的工地那边。”又问起我爸,她说:“去城里接你两个侄儿咯,现在是放学的点儿。”我本来想接着问既然我家人都不在怎么她在这里,想想挺不礼貌的,便忍住了。
一路劳累,跟碧珠娘说了两句话,我上楼去自己的卧室睡了一觉。醒来时,夕阳的余光在玻璃窗上闪动,我又下楼,家人还是没有回来,中午在火车上没有吃饭,肚子有点儿饿。厨房的桌子上有一袋苹果,我拿出一个来,本来想找刨子刨了皮再吃,半天没有找到,只好洗了一下开吃。走到我父母的卧室,碧珠娘还在看电视,大概是我吃苹果的声音太大,她又转头看我,“你么不刨皮?”我说没有找到,她立马起身说:“就在碗柜里,我给你拿。”说着她让我跟她进了厨房,打开碗柜,第二个格子里,她手一伸,果然就有了,“喏,你看!”我手上的苹果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她又从桌子上拿出一个大的来,刨好皮后把刨子递给我:“你自家刨。”说着她一边啃着苹果一边又去了卧室。
我拿把凳子坐在门口吹风,垸里看起来空荡荡的,大家都还在地里干活,或是去工厂上班,陆陆续续地开始有人骑着电动车回来了。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天刚擦黑,母亲第一个回来,我叫她,她又高兴又惊讶,“你么回来了嘞?”我说了原因,她点点头往家里走,“我先去换身衣裳,再去村里买点儿肉。”她身上穿的衣服是父亲以前穿破旧的,方便她在工地上搬砖。我说:“碧珠娘在看电视。”母亲“嗯”的一声,没有多说什么就进去了。碧珠娘的声音很快响起,“花姐哎,你么这会儿才回?庆儿都等了好几个小时咯。”母亲说:“我也不晓得他要回。”
母亲换好衣服正准备去村里时,父亲也骑着电动车回来了。车子刚一停,大侄子和小侄子从后座跳下来,见我打了一声招呼。刚进堂屋,小侄子喊了一声,“她为么子又在这里?”母亲忙呵斥道,“莫瞎说,赶紧上楼做作业!”小侄子不满地噘着嘴,跟着他哥哥上楼了。反正无事,我便跟母亲一同去村里。天已经完全黑了,路灯亮起,我挽着母亲的手,慢慢往村里的超市走去。我问起碧珠娘的事情,母亲说:“我都习惯咯。她这样都快一个月咯。我也不晓得说么子好。”
碧珠娘跟母亲出嫁前都是同一个垸的,从小就相互认识。后来我母亲嫁到我们垸里来,她也随后嫁给了我们垸的来运爷,过了两年她妹妹彩珠又嫁给了我们垸的任丘爷,因着这一层关系,大家都走动得特别热络。碧珠娘跟来运爷生有一儿一女,儿子云峰跟我从小是同班同学,现在在广东打工,女儿云霞嫁到外地去了。两年前,来运爷去世,碧珠娘自己一个住在家里。以前我们家还住在老屋时,离碧珠娘的家近,她时不时会到我们家,跟我母亲聊天。后来,我们在垸后头盖了新屋,她来的就少多了。
一个月前的一天,外面在下雨,母亲正坐在卧室里看电视,她突然过来了,也没什么事情,就是实在无聊了过来转转。母亲问她怎么不在武林的麻将馆打牌,她拍拍自己的口袋,母亲知道她是钱输没了。碧珠娘是个爱牌之人,基本上每次去武林麻将馆,都能看到她在打麻将,嘈嘈杂杂的声音里,经常能听到麻将牌拍在桌子上“啪”的那一声脆响,“娘个屄的,清一色!”高亮的声音透着振奋,碧珠娘自豪地把面前的牌推倒,让牌友们看仔细了,“终于和了一把!”牌友们唉声叹气,她则笑得拍手,“你那个二饼一出,我就晓得我要成咯。”这一盘,她可以进账一百多。牌玩得很大,赢得多,输起来也狠。母亲说起有一次碧珠娘输了几千块拿自家的棉花做抵押,还忍不住啧嘴。
母亲这次没有问她输了多少,端来点心和瓜子,一边看电视一边闲聊。门外春雨淅淅沥沥,新屋这边邻居少,也无人来,父亲不知道去哪里打牌了,侄子们还在学校。到了中午吃饭的点儿,母亲起身去做饭,碧珠娘没有走的意思,母亲做饭便多加了她一份。饭做好了,叫她,她也没推辞,两人在厨房吃了一顿。母亲洗碗,她又到卧室看电视去了。到了下午,雨停了,母亲想去田里看看,跟碧珠娘说了,碧珠娘安坐在沙发上没有动弹。母亲去后厢房换好衣服,拿了锄头,碧珠娘还在那里。母亲说:“碧珠,我要出去了。”碧珠娘眼睛没有离开电视,挥了挥手,“你去吧!我把这集看完。”
等母亲从地里回来,已经是下午五点了,一进门,电视还在开着,碧珠娘已经歪在沙发上睡着,一地瓜子壳。母亲怕她冻着,拿毛巾给她盖上。做好晚饭,父亲接两个侄子也回来了。菜端上了桌,母亲又去卧室,见碧珠娘已经醒来,正对着电视发呆,便叫她一起吃晚饭。碧珠娘说好,跟着母亲一起到了厨房。吃了晚饭,父亲出门玩去了,侄子们上三楼看电视,母亲也开始收拾碗筷刷锅洗碗了,碧珠娘依旧没有走的意思,坐在饭桌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母亲说话。
嫂子到晚上九点之后才下班,所以在此之前,母亲会去三楼照看两个侄子。等嫂子回来,侄子们也都睡了,母亲才下楼到自己的卧室休息。这次把灶台都擦拭干净了,又把地给拖了一遍,出门倒了垃圾,碧珠娘还坐在那里。母亲没办法,跟她说,“我要到三楼去咯,你要去看一下么?”碧珠娘连忙说好啊,跟着母亲上去。侄子们做完了作业,正在客厅沙发上看动画片。母亲跟碧珠娘也坐下了。看了不到两分钟,碧珠娘说:“这动画片有么子好看哩!”说着拿起遥控器,换到了电视剧频道。两个侄子嚷着抗议,母亲高声说:“莫闹!人家是客人,要懂礼貌。”侄子们气哼哼地嘟囔了两句,都去房间玩了。
碧珠娘看着看着打起瞌睡来,有时还发出细细的鼾声,母亲推推她,“碧珠,你要不回去早点儿休息?”碧珠娘一个激灵醒来,木木地看着母亲,母亲又说了一次,她摇摇头,“没得事了,我不困。”母亲不好再说什么。到了九点多,母亲听到楼下停车的声音,知道我嫂子下班回来了,一想到要是让她看到有外人坐在这里也许会不高兴,便忙推醒碧珠娘,“我媳妇回咯,你要不明天再来看?”碧珠娘费力地睁开眼睛,看看母亲,一脸懵懂的神情。母亲又说:“我媳妇儿回咯。”碧珠娘“哦”了一声,没有起身,“玲儿回来了?”母亲点头,“你要不明天再来?”碧珠娘慢腾腾地起身,“好啊,那我明天来——”正说着,嫂子已经进门了。嫂子并不认识碧珠娘,母亲尴尬地介绍一番后,她点头笑笑,进房间看两个孩子去了。碧珠娘又坐下,母亲这下急了,“我也要睡了。”碧珠娘这才彻底起了身,回去了。
第二天晚上,母亲在三楼督促侄子们写作业,碧珠娘又上来了。电视没开,碧珠娘“咦”地一声,“36集开始咯,为么子不看?”母亲说:“这两个细鬼,作业还没写完。”碧珠娘坐在沙发上,“噢,那是要抓紧写。”说着拿起遥控器,调到了要看的那个频道。侄子们写写,又抬头看电视。母亲说:“好好做作业!没做完,你们妈妈回来又要打你们。”大侄子回道:“电视声音太大了。”母亲为难地看过来,见碧珠娘并未察觉,只好说:“碧珠,要不你到一楼去看。”碧珠说好,母亲带她下了楼,到了一楼卧室,父亲正在看新闻。碧珠娘忙说:“新闻有么子好看的,电视剧正放到要紧处咯。”父亲惊讶地看着碧珠娘拿遥控器换到了电视剧频道。父亲想说什么,又忍住了。
嫂子下班回家后,见到母亲的第一句就说:“那个碧珠娘,为么还在那里?她为么不回自己家?”母亲说:“她家里没有电视机。”嫂子奇怪地问:“现在电视机又不贵,几百块钱就能买一个。”母亲点点头,“是啊,我跟她说过,她说又要上街去买,又要牵闭路线,太麻烦。”嫂子一听笑了,“这个也嫌麻烦啊?想不到。”母亲继续说:“你没看到她家里的那几亩地,她几乎从来不去看一眼的。地里全是草!有时她还问问我,地里还有棉花吧。你说叫我么样说,自家屋里的庄稼不管不问。只晓得天天打牌,输了钱就向儿女要。”嫂子说:“我要是她儿女,我会烦死!”母亲“嗯”了一声,“她女儿老是被要钱要烦了,有一次跑过去把麻将桌都掀翻咯。两个人吵了一架,女儿从此以后就不跟她来往了。她儿子,在外地,也不愿意回来,说她虐待他爸爸来运。”
来运爷中风后,瘫痪在家,母亲有时经过他家,听到他的喊声,“碧珠——碧珠——”喊了几声无人回应,进去一看,他从床上跌落下来,瘫在地上无法挪身。来运爷是一个高大的男人,母亲想帮忙抱起他,也无能为力,只好让他先等着。到了武林的麻将馆,碧珠娘果然在。母亲走过去说:“你家来运摔到地上了,拉了一裤裆屎,你快回去看看。”碧珠娘猛一拍桌子,“他为么子来搞这些事儿!他的衣裳我昨天刚洗了一桶,他又给来这一出。”有个牌友说:“你还是回去看看嘛,都这个样子,又不是人家自己愿意。”碧珠娘伸出手给大家看,“你看看,你看看,我手肿得跟萝卜似的!天天给他擦身子洗衣裳,还要给他喂饭送水,端屎倒尿,这是么样的日子?这就是地狱啊!”母亲催她回,她恼了,“不回不回!他趁早死了算了。”其他牌友都劝她,“你还是回去看看,人家也造孽!”她说,“他造孽,我不造孽!”嘴上这么说,还是起身回去了。
半年后,来运爷去世。云峰和云霞都回来了,葬礼过后,他们跟碧珠娘大吵了一架。云峰说起爸爸在生病的时候想喝水,喊了半天,都不见她踪影;想吃口饭,也不见她给口热的;天天只晓得搓麻将,图快活。碧珠娘气愤地反驳回去,“你们说我虐待,你们自家嘞?躲得远远的!哪回看到你们回来,给你们爸爸洗过身子,端过屎,倒过尿?现在有么子脸皮说我的?”这一架吵完后,云峰和云霞当天就离开家,过年也不回来了。
说完这些,嫂子也准备洗漱休息了。母亲下楼来,走到卧室门口,碧珠娘靠在沙发上睡着了,父亲躺在床上靠着背枕也睡着了,电视还开着。母亲推醒碧珠娘,让她回去睡觉。碧珠娘说好,磨磨蹭蹭地起身。打开大门,夜晚的凉风吹来,碧珠娘抖了一下身子,“这么晚了!”母亲说:“你路上小心。需要电筒吗?”碧珠娘说要,母亲便去房里取了电筒给她。她把手电筒拿在手上,掂了掂,低头想了想,然后说:“我回去咯。”母亲心忽然一软,“明天你再来看。”碧珠娘说好,雪亮的电筒灯光从夜色中辟出一条路来,她上了水泥路,没有往自己家的方向走,却走上了另外一条路。母亲一看,是通往武林的麻将馆。
(二)
走到村口时,母亲突然说:“我有点儿后悔说那句话。”我说什么话,母亲说:“就是让她明天再来看电视的话啊,么人晓得她一个明天两个明天,都一个月咯。”我忍不住笑了出来。母亲瞪我一眼,“你还笑?有时候我几不愿意做饭的,在工地上累得要死,回来就想随便泡点饭吃算了,但是人家在,你又不好意思让人吃冷饭,我又打起精神来重新做饭。”我叹了一口气,“你直接跟她说嘛,哪里有在别人家吃喝这么长时间的,她自家都不开火?”母亲说:“她还真不开火。她家灶屋屋顶都塌了,哪里去做饭?她也懒得叫人去修。”
过马路,进了毛兵超市,母亲走到生肉柜那头,准备买几斤猪肉。我跟在母亲后头,忽然有人来拍我肩膀,我一看,是彩珠娘。她笑了起来,“我说为么子这么眼熟,还真是你啊。”她又捏捏我的手臂,“你又胖啦,看来外面油水好。”我说:“我要减肥咯。”她说:“有么子好减的?胖胖巴巴的,有福气。”她手上拎着一袋剁好的排骨,我不由分说地拿过来给她拎着,她说:“还是你好啊,不枉我心疼你一场。”小时候母亲没奶,彩珠娘常把我抱过来喂奶。
母亲买好了肉,见彩珠娘,也笑了,“你倒是好精神,又买排骨。”彩珠娘撇撇嘴,“哪里是我要吃?我屋儿媳妇不是有了么……”说着看向我,“你么会儿带个女伢儿回咯?”我说:“我不急,我还小。”彩珠娘轻轻打了我手臂一下,“净瞎说!你还小?!全垸就你和我屋云峰,还不说亲,你老娘么不急?你要说云峰屋里这个样子,她老娘,”彩珠娘哽了一下,“又这么样,说不上亲是没得办法,你条件好好的,要抓紧咯。”我忙说好。彩珠娘想起什么来,扭头问母亲,“我姐这段时间是不是经常在你那里?”母亲说是。彩珠娘啧啧嘴,“没得办法!么样说她好嘞?!”
母亲买的肉,我也给拎上了,彩珠娘挽着母亲在我旁边走。母亲说:“你姐还不理你?”彩珠娘说:“她啊,还不是为了云峰的事情。年前云峰给我五千块,叫我帮忙把他家那个灶屋屋顶修一下。我就跟我姐说这个事情,她一听倒好,非要我把五千块给她。她也不想想云峰为么子不肯直接把钱给她,还不是怕她跟以前一样,一赌就全部输光咯。她就说,钱不给她,她宁愿灶屋这么塌着。我就跟云峰说这个事情,云峰一再让我把钱守住,莫给她老娘。这下好了,我姐就以为是我故意扣着不把钱给她,跟我记上仇咯。”
我插嘴问彩珠娘,“那没有灶屋她去哪里吃?”母亲看了我一眼,“你说嘞?”我一下子明白了。彩珠娘声音越说越大,“你这是第三家咯。之前天天跑我屋里去,我们在吃饭,她就跑来,说反正她儿子的钱在我这里,她一定吃回来。你说气不气人?但这是我亲姐,我能说么子?吃就让她吃呗。总不能看着她天天在武林那麻将馆吃方便面。人家会说亲妹在一个垸里,都不管她。吃了四十五天,我媳妇儿是在受不了咯,就跟她说不能天天这样,她就气到了,说是我挑拨的。唉哟,气得我呕血!她来是没有再来,结果跑到枫林家里,在人家屋里看电视看得太晚,人家吃饭她也跟着吃,吃了一个月,枫林家里的人也说话了。她又跑裕华屋里,又是这样。我没想到,她现在又到你屋里去了。”
彩珠娘说着说着颓丧起来,“我也不想管她咯。凭么样对她好,人家都说你不是。”母亲沉默一会儿,说,“想想人家也可怜,无依无靠的。”彩珠娘激动起来,“有么可怜的?同样是寡妇,你看看人家王凤,屋里整理得干干净净的,还种了七八亩地,顾自家吃喝没得问题,还跑到榨油厂打一份工,你看人家还不是活得好好的。”母亲又宽慰了她几句后,渐渐无话,水泥路上只有我们走路的声音。到了我家附近,彩珠娘向我家探头看了一眼,“她还在?”母亲瞅了一眼,“在,我都听得见她的笑声。”
彩珠娘从我手中接过排骨,待要走,又没走,从口袋里摸出几百块钱,塞到我母亲手中,“实在是过意不去,这几百块你拿着,就当是她这么长时间的伙食费。”母亲忙把钱还过去,“你这是搞么子鬼?!都是自家人!”彩珠娘又把钱塞到我手上,“接咯!”不等我说话,转身快快地走开。我去追她,她转头说:“你不听话是啵?再过来,我生气了!”见她语气很重,我只好停在那里,回头看母亲,母亲叹了一口气,“回去咯,以后我再找机会还她。”
黄瓜肉丁、煎茄子、西红柿鸡蛋汤,再配上几道凉菜,便是晚饭的全部了。摆好碗筷,母亲上楼去叫两个侄子,我去一楼卧室去叫我父亲。正在放《新闻联播》,父亲不在,碧珠娘靠在沙发上,倒是没有睡着,眼睛盯着电视,可感觉更像是发呆。我问了一声,“碧珠娘,我爸呢?”她回过神来,“我不晓得哎。”她鼻子嗅了嗅,“饭熟咯。”说着起身往厨房走。我仔细打量了她一番:她本来个子就很小,现在年纪大了,人更像是缩小了一号,衣服松垮地挂在身上,上衣还是我跟云峰上中学时穿的校服,里面衬衣的领子一个在里,一个在外,裤子上沾了很多棉絮,她也没去管;花白短发,眼袋沉重,皮肤暗黄,走起路来却是急急的,更接近于小跑了。
饭桌上,侄子们已经在吃了。碧珠娘自己打开碗柜,拿出饭碗,去灶台盛饭。母亲正在刷锅,回头见两个侄子端着饭碗要上楼,“好好吃饭!不要乱跑。”大侄子说:“我不要跟这个人一桌!”母亲说:“么样说话哩?!”侄子们不管,径直上楼了。碧珠娘碗拿在手中,迟疑地看了看,想放下,又没放下。母亲忙说:“细伢儿不懂事,你莫见怪。”碧珠娘短促地笑了一声,“不怪不怪。”身子还呆滞在原处。母亲又说:“你快去吃,饭要冷了。”碧珠娘没有看母亲,端着碗走到饭桌边上。
母亲刷完锅,又扫地,饭桌上只有我和碧珠娘。她小口小口地吃饭,没有去夹肉菜,一直吃着面前的茄子。我不知道跟她能说什么,埋头吃自己的。“你这次回来,给你老娘带么子吧?”她突然问我。我抬头,她没有看我。我说:“临时起意回来,来不及买。”她“嗯”的一声,“那你给你老娘钱就好咯。”我说晓得了。又无话,只有筷子碰到碗口的声音。她忽然又说了一句:“云峰就不给我钱,宁愿我饿死。”我说:“等他过年回来,给你带钱。”她“嘁”的一声,“他才不回,我在屋里死得生蛆,他也不会望一眼的。”我尴尬地笑了笑,“不会的。”她把筷子搁在碗口上,“你等看。我也活不了两年了,他也巴不得我早死。”
母亲忙完,端了饭来吃,见碧珠娘起身,便说:“你坐你的,我坐这边的位置。”碧珠娘说:“不咯,我回去了。”母亲讶异地看了她一眼,“你,不看电视了?”碧珠娘摇摇手,“看烦咯。我想让庆儿帮我一个忙,”她看向我,“可以啵?”我站起身来,“可以哎,你说。”碧珠娘连忙过来拉我的手,“在我屋里,你跟我去一趟就行咯。”母亲说:“么子事儿,搞这么神秘?”碧珠娘冲我母亲摆摆手,“你吃你的,要不了半个小时。”母亲放下碗筷,去堂屋把手电筒拿过来递给我。碧珠娘连连推我,“好好好,走走走。”母亲说:“碧珠哎,鬼赶你是啵?”碧珠娘回了一句,“莫瞎说,多黑天,吓死人!”
(三)
天果然是黑,手电筒快没电了,灯光微弱,没一会儿就熄灭了。借着朦胧的月色,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在碧珠娘后头,越发感觉她的小,她急急地往前搓,走得却不远,我几下子就赶上了。她问我工资有多少,又问我谈女朋友没有,问完了,也答完了,沉默又一次降临,她开始擤鼻涕吐痰。从一排茅厕穿过,走个十来米,就是她的屋子了。看得出原来是要盖两层的,却没有盖起来,二楼只有在楼梯口处盖了一间小屋子。靠近主屋边侧,单独盖了一间,应该是灶屋。走到门前,碧珠娘推了一下,门随即就开了。我问:“门为么子不锁?”碧珠娘往里走,“有么子好锁的?又没有么子东西可以偷的。”
没有电灯,碧珠娘说电费很久没交了。我突然想起我手机上有手电筒的功能,遂打开,碧珠娘借着光找到了一根蜡烛,又四处找火柴。我问:“你平常时回来,么办?”碧珠娘说:“回来倒头就睡,根本不需要灯。”堂屋没有找到,又摸着去灶屋,一进去,风迎头压过来,一抬头能看到天。原来是屋顶中央塌了一部分,灶台上还有摔碎的瓦片。碧珠娘打开碗柜,有老鼠咻地一下从她手边跑过去,吓得她叫了一声。终于在灶台下面找到了火柴,我们又到了堂屋,火柴一刮着,随即被楼梯口灌下来的风吹灭。我们又到了卧室,这才点着了蜡烛。
借助蜡烛微弱的火苗,我看了一眼卧室,只有一张床,一条凳子,一个立柜,一个小桌子,再无其他。墙壁是裸露的红砖,地面是泥地,走在上面感觉凹凸不平。窗户上的玻璃碎了好几块,有男人的衣服堵着,我想那衣服可能是来运爷生前穿的。一想到“生前”两个字,我刹那间汗毛竖起,房间太大太空,烛光无力地摇曳,而夜色浓稠得搅不开。大门吱嘎吱嘎响,我吓得不敢看房门口。碧珠娘先打开立柜翻找,没有,又去桌子上找,还是没有。我问她在找什么,她说在找云峰的电话号,她记得是写在一个本子上的。她又走到床边翻找,被子一掀开,随即有东西掉下来,一看是好几个方便面袋子,床单发黑,中间裂开,露出里面发黄的棉絮,枕头原来应该是蓝色的,现在也是黑黢黢的,在枕头下面,她找到了那张写有云峰手机号的本子。
“你帮我打一下。”她把本子递给我,“我打电话,他无论如何都不接。你们是同学,以前玩得也好,你说话他应该能听的。”我问:“那我要跟他说么事?”她想了想,说:“就说老娘快要饿死了,没得饭吃的,让他可怜可怜老娘。”我又问:“是让他打钱?”碧珠娘说:“我没得银行卡。让他回来一趟,我都快活不长咯。”我不知道最后一句是真的,还只是她希望云峰回来用的策略,我拿起电话,拨打那个号码时,碧珠娘盯着我按键的手,她身上一股很久没有洗澡的臭气隐隐盖过来。
云峰接了电话。说实在的,已经十来年没有跟云峰联系过了,乍一联系,还真不知道说什么好。跟他寒暄了几句,他问我为什么想起跟他打电话,我瞥瞥碧珠娘,“你妈想跟你说两句。”碧珠娘拼命摇手,又用手指我,看她意思是让我来说。云峰一听是他母亲要我打过来的,本来轻松的语调一下子紧绷起来,“她又要搞么子鬼?!”我一下子噎住了,很无奈地看着碧珠娘,把手机也递过去,“还是自己来说吧。”碧珠娘吐了一口气,接过手机,劈头一句,“活贼哎,我不联系你你就永远不联系我是啵?我要死了,你是不是望都不望一眼?!”我拉拉碧珠娘的衣袖,“有话好好说。”
碧珠娘拿着手机,弓着身子,大声地唾骂。我站在一边,听着风在堂屋里回旋,像是一个肥胖的巨人在寻找出口,有老鼠在床底哪个地方吱吱乱叫,放在桌子上的蜡烛烧尽了,房间又陷入沉沉的黑暗之中,唯有手机是亮着的,映出碧珠娘愤怒的脸。“孽畜哎!孽畜哎!”碧珠娘的声音都喊劈叉了,“你么不说话了?你晓得羞愧啊?你个孽畜!你说话哎!”她对着手机吼,“说话!”我见不对劲,凑过去看手机屏幕,“碧珠娘,云峰已经挂电话咯。”碧珠娘拿手机的手一直发抖,身子也在抖,好一会儿,她把手机递给我,“你再拨过去!我话还没说完!”我迟疑了一下,她大声喊着,“你拨过去!快点儿拨!”我吓得往后退了一步,电话拨打过去,对方已经关机。
碧珠娘喘着粗气,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一不小心撞到桌子上,她一脚把桌子踢倒,“孽畜!孽畜!”我不敢动弹,她又继续转,“都不管我!都不管我!我去死算了!去死!去死!”我鼓起勇气上前止住她,“碧珠娘,我明天再打。你莫生气。”她怔怔地看我,停住了,随即整个身体像是筛糠似的,“哎哟,没得意思。”她像是丧失了所有的气力,一下子瘫在地上,“没得意思。真没得意思。”我说:“要我把你扶到床上啵?”她没回答我,一直在大口地喘气,“哎哟哎哟,没得意思哎!哎哟,哎哟——”她一会儿揉着心口,一会儿打自己的腿,“都不管我。都不管我。”
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想抱她到床上休息,手一伸过去,她就叫,“莫管我!莫管我!”在一边看着,更是着急。正手足无措之时,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喊我名字,一听是母亲的声音,我赶紧答应了一声。很快,一束雪亮的灯光穿了进来,拿着手电筒的母亲打量了一下我,我忙说:“你看碧珠娘!”她看过去,碧珠娘躺在地上不断叹气,“她出么事咯?”我说了一下事情的大概经过,母亲点点头,把手电筒递给我,她蹲下身去拉碧珠娘。“莫管我!莫管我!让我死了算了!”母亲不管,依旧拉她,还是拉不动,便冲我说:“过来帮忙!”我们两人把她抬起,放在床上。
她在床上缩成一团,叹气没有了,变成了呜咽声。母亲捏住她一只手,“有么子大事?至于这样?”碧珠娘哽咽地说:“我晓得你们都讨厌我。我心里跟明镜儿似的,可是我有么子办法?我自家也不想这个样子的。”母亲靠得她更近了,“么人讨厌你?你看我说过你半句不是?只是你自家也要争气才是。”碧珠娘没有说话,她想想又哭起来,哭完又想想,母亲一直捏着她的手,说着些宽慰的话。碧珠娘渐渐没了声音,再一看,睡着了。母亲起身说:“碧珠,那我们回去了啊。”没有回话。
我陪着母亲出了卧室,母亲拿着手电筒扫了一下堂屋,光照到堂屋正中间的墙壁上,一张人脸浮了出来,我们都吓了一跳,再一看是来运爷的遗像挂在那里。我心里特别害怕,连忙催母亲赶紧走,母亲小声地说,“来运都死这么长时间咯。”我忙说:“莫说咯,怪吓人的。”走到门口时,我把手机放到口袋,顺手摸到了几张纸币,突然想起来这还是彩珠娘塞给我的。我跟母亲说了这个事情,母亲说:“你把这钱放到她卧室里去。”我说好,借着手机的光亮,又进了卧室,桌子已经被碧珠娘踢散架了,我只好把钱放在立柜上面。走之前,看了碧珠娘一眼,她把头埋在被子里,发出细细的鼾声。
大门怎么都关不上,一看是门栓坏了,我们只好放弃。夜已深,路两旁的人家都已经关灯睡觉了。月光反而明亮起来,树影在水泥路上舞动,走着走着,像是在海底。我挽着母亲的手,母亲笑道:“你么长不大哩?”嘴上虽然这么说,还是让我挽着。走着走着,母亲转头去看碧珠娘家,那塌了屋顶的灶屋露出横梁来,啧啧嘴,“这个屋子住不得。”我说:“我觉得也是,在里面我都觉得害怕。”母亲说:“可那有么子法子嘞,她能搬哪里住?”沉默了一会儿,她接着说,“她那个被子能捏出水来,我明天给她一床新的。”说着话的时间,我们马上就到家了,我问母亲,“你说碧珠娘明天还会不会过来看电视?”母亲说:“么人晓得嘞?也许会来,也许她会换一个人家去。”
PS:选自《我认识了一个索马里海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