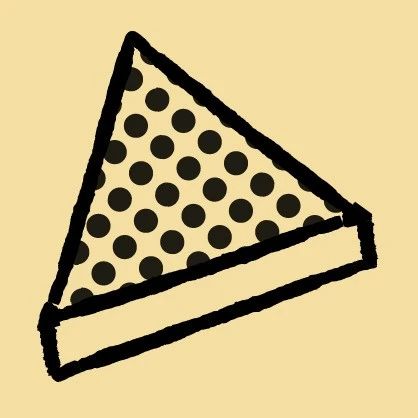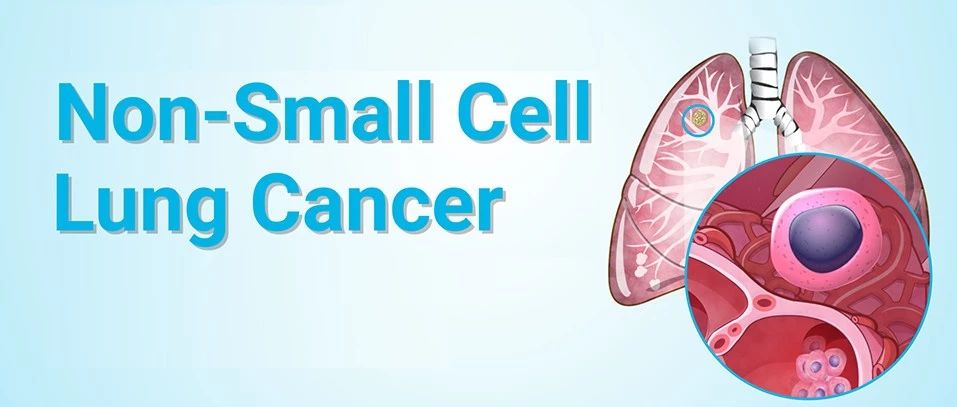1.
夏夜,跟编剧岳小军约在南锣鼓巷聊剧本。穿过天真疲惫的情侣游客,交替呼吸着炸臭豆腐,烤羊肉串,古老公共厕所和潮湿槐树皮的气息,终于找到一家一个客人都没有的酒吧。老板五十多岁,不苟言笑,光着膀子戴着大耳机坐在电脑后快速敲着键盘。我们要了酒,学着老板打开电脑,开始有一搭没一搭的讨论。外面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一阵喧嚣之后,门外的胡同空无一人。我们没带伞也没话可说只好继续叫酒坐等雨停。老板一直严肃地收发着永不消逝的电波,屏幕的光在他脸上闪动,天空中也电闪雷鸣。喝着喝着有些醉了,我们又回到卡住的地方继续讨论,仍然没什么进展,不知道什么时候雨停了,朝霞也出来了,我们决定回家睡觉,晚上再说。去吧台买单,老板从电脑后起身,摘下戴了整晚的耳机,收完钱后突然感叹:“你们的奔头是往前看的,我的奔头是往回看的。”我瞥见他的电脑屏幕上同时开了好几个视频窗口,里面是一些还在说话或打字的女人,和我们一样疲惫。
出了门低头走着,胡同被雨水洗的闪闪发光。差点和一群叽叽喳喳去上学的小学生撞个满怀,我问他们:“你们是哪个小学的?”孩子们好像要把我从明显的倦意中唤醒,高声齐答:“黑芝麻小学!” “重点小学吗?” 一个快乐的小胖子抢答:“普通!但是可好了!”说完都笑着追赶着跑开,我在阳光下眯着眼睛看了好久。
2.
河西走廊的移民村,我和小军徒劳地跟警惕的村民们解释着什么叫“采风”。其中一位悄悄把我们请进村委会办公室,几个人围上来悲愤地控诉他们因为老家修建水库背井离乡被安置到这戈壁摊上的遭遇,几瓶白酒“哗哗”倒进大碗,妇女主任端起一碗一饮而尽,客人只好入乡随俗喝了起来,一厚叠申诉材料塞进我手里,慢慢明白他们把我们当作了中央派来了解情况的记者,越否认他们就越觉得我们带着更重要的任务。门“咣”的一声撞开,一位不知怎么听闻有陌生人来访的乡干部进屋解救了已经被灌得语无伦次的我们,乡亲们一边眨眼一边顺水推舟把我们送上他正要回城的车,我把那叠材料偷偷塞进了书包。一路上干部滔滔不绝介绍着本地的建设成就,晕晕乎乎就被拉到县城一家餐厅,又是一通白酒羊肉,席间干部一直夹叙夹议刁民难管乡官难为。我用最后的清醒强行买了单,干部也不再热情追问我们的行程安排互道谢谢消失在夜色里。
回到北京把材料交给律师朋友,他研究之后的结论是官民双方都有道理和问题,即使走法律程序也难分胜负。他告诉我,干部关心我们是不是可能败坏地方形象的记者,一番摸底之后,看到我们又坚决买单应该释怀了。
3.
赵总坐在对面,小廖坐一侧,前所未见地严肃:“赵总特别忙,你言简意赅点儿。”我打开电脑里终于定稿的剧本正要说话,赵总拿起一只生蚝一口吸了进去:“你不介意我吃你说吧?我只有半个小时时间,待会儿我走了你再好好吃。”我开始介绍剧本里的每个人物,赵总边吃边听,似乎挺有兴趣。我说到第三个人物,他向后挨上了这间豪华餐厅的舒服皮沙发的靠背,一个老外服务员给他的杯子加了些酒,赵总打断了我:“这么多人物记不住啊,你简单说说故事吧。”我只好转向梗概,一句话没说完,进来一个中年人跟他耳语了几句又出去了。赵总直起身:“不好意思,我只有十分钟了,这样吧,你告诉我你这个电影像哪个著名的电影,古今中外都行,我让小廖帮我买碟看看。”“我不希望像哪个,只知道是什么。”“是什么根本不重要,在咱们这种国家,除了餐饮业,做不出任何独一份的东西,做出来也没人认。”赵总有些恨铁不成钢:“比如我们做手机,要么像苹果,要么像三星,不可能去做一个中国独创的手机,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当然怎么吆喝是另一回事儿。”我不知道怎么回应,赵总起身拍拍我的肩膀:“这家的挪威海鲜特别棒,你好好吃,想好了让小廖约我再聊。”赵总雷厉风行走了,小廖分析判断叮嘱了一会儿,我们也散了。
几个月后,小廖打电话给我:“想好了吗?”我:“还没。”又过了一段时间,小廖又打来:“赵总对你印象很深,这样的投资人很难得,你随便说几个片名我去找找。”我:“我试试。”他:“等你电话。”我:“好。”从此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4.
这只两米多高的鸵鸟安静挺立在围栏里,它不像它的同伴那样人往左走就跟着往左人往右走又跟着往右,西北烈日下,它小小的脑袋上大大的眼睛如相机快门般一眨一眨地,深思熟虑又警觉的样子让人晕眩。我和小军商量好了,如果河西走廊看不到养鸵鸟的,我们就把剧本里的主角二勇的职业改了,结果采风第一站就歪打正着来到这间好像坐落在火星上的破败鸵鸟场。突然一阵微风吹来,它三百多斤的沉重身体轰然倒地,没有一丝挣扎死了。工人们过来拖走尸体,留下一根羽毛贴地翻飞。初见是它的弥留之际。
拍摄日。两只鸵鸟先后狂奔逃脱控制,监视器里两次看见道具组同事以惊人的速度跑过出画追赶,鸵鸟总领先五六米的距离,稳健匀速地消失在沙丘后,追鸟人两次都是精疲力尽瘫坐在地上,缩成一团远远的剪影。只能换备用鸵鸟再拍。当天下午,组里的皮卡找回了一只。三天后一个月朗星稀狂风怒号的深夜,看守我们在沙漠里搭建的鸵鸟场外景地的置景同事被急促的敲门声叫醒,一位骑摩托车过来的老乡带来了好消息,他在沙漠深处某地发现了另一只鸵鸟的下落,但开价两千块信息费,尽管半信半疑,考虑到可能为剧组挽回六千块的损失(当地市价一只八千块),置景同事当即现金成交。几个小时的颠簸车程后,大家在老乡准确无误的带领下来到一条也许干涸了上百年的河床边,天已经亮了,那只鸵鸟万念俱灰安静趴在岸边,不再反抗,晨曦给它镶了一道金边,大伙儿毫不费力把它架上车带回了营地。没有人问那位老乡为什么深夜会在沙漠里游荡,不知道他不带任何工具是怎么辨别方向和定位的,他也没说如何遇见了鸵鸟。很久以后想起来,我们已经搭景工作了一周的时候,当地文物管理部门以那片沙漠地下有汉代墓葬群为由叫停了工程,后来只好整体拆装征得批准向南挪了两公里从头再来。
5.
我的朋友勇哥是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兰州厨师。我请他喝啤酒,他用兰州普通话帮我修订台词。我读剧本对白他口述校正,我再记下来,有时候我们会停下来讨论。我读了一句话给他听,“因为……所以……再所以……”很简单的逻辑。“啥?”我解释了一遍。“听不懂。”我换个说法又解释了一遍。“听懂了。”“行吗?”我问。“不行,你说的这个兰州人不这么说。”“咋说?”勇哥放下扎啤杯,真诚地看着我:“日。”我连忙记了下来。
勘了一天景回旅馆,手机都没电了没法导航,制片助理把车停在路边,探头问一位坐在门口休息的慈眉善目的老者:“大爷您好,请问您过了桥那是不是兰州军区招待所?”大爷头都没回:“你不过桥那也是兰州军区招待所。”
6.
从北京回到外景地。一下车就被戈壁的狂风吹得趔趔趄趄。美术组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快一个月了。看见我们年轻时尚的美术指导覃伟立还是很有型,古铜肤色和敏捷的动作让他多了几分匪气。细看太阳镜上满是砂砾的划痕,头发像野草一样枯涩但修剪得层次细腻,意大利手工皮靴被泥土做旧得如同楼兰古物,闪亮的爱马仕丝巾上羊油斑斑。他在旷野的风中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对着电话怒吼安排着工作,间歇问候了我:“回来了?”“回来了。”他拉开拉链开始小便:“严丝合缝照着我的制作图去做,做不了就走人!”尿意盎然的我正要如法炮制,“方向错了!”伟立对着我一声断喝切换回了现场。好险,差点逆风尿自己一身。我调整成了一样的方向,有些纳闷才离开了几星期就不熟悉这风了,一瞬间风的形状,质感和声音突然又变得清晰真切了起来,淹没了一切。
7.
深夜的篝火烧得更旺,录音指导王砚伟的十几只话筒已经支好,营地清场完毕,必要的工作人员都找到地方坐定,马条老师(请原谅后来我剪掉了你的这场戏)喝了点酒,在火边抱着吉他示意可以开录。“OK”的手势在火光里传递,开机的红色指示灯亮起。吉他的拨弦声和风声,柴火的“噼啪”燃烧声混在一起渐渐从夜色中升起,然后是他叙述回忆的歌声。直到一只掉队的大雁不知从哪儿飞到我们头顶,开始盘旋鸣叫,没有人忍心把它赶走,制片大叔也变得很温柔,嘱咐大家休息一会儿,他拿来了一些酒,大家静静喝着听着马条老师没有停下来的弹唱,有人跟着音乐微微摇摆身体,有人一直抬头望着这只迷路的大雁,有人石像般一动不动,也有男孩和女孩偷偷相视一笑又躲开目光。半个小时后,大雁低鸣着飞走了,闲暇时光结束,工作继续。那个夜晚和那些跳动着火光的纯洁的脸将一再浮现,但唯一的证据是现场同期录制后来被混录进成片里的大雁的鸣叫声。
8.
“冬不拉?”作曲陈弘礼提议。“诶,不错啊。”我特别兴奋。“找谁弹?”我问。“我试试。”他目光狡黠。我们在讨论用独特的音色来呼应而非渲染铺陈这些失意挫败的人物走在各自路上暗想那条没走的路的心境和思绪。他起身从屋里的乐器收藏里拿出一把漂亮的冬不拉。这是多年前他从日本带回来的,一个哈萨克斯坦的老艺人纯手工制作而成,擦干净灰尘,它要第一次进入录音棚。“他们遇见又分开……”“我知道你的意思。尺八。”他盯着我。亚洲腹地草原流传最广泛的两根羊肠弦的游牧民族弹拨乐器,从中国江南辗转漂泊到日本的竹质吹管乐器。曾经是摇滚乐队主音吉他手和音乐学校吉他老师的弘礼弹冬不拉,一位民乐团的专业笛子演奏家吹尺八。两个寂寥的动机各自发展变奏,没有合奏却始终遥相应和,其他的钢琴,打击乐,吉他从这个对话关系弥散开去,所有的音乐都要节制,不知所起又戛然而止,一如这些人的聚散,一如这部电影的核心意象:一大一小两个Loser在茫茫黑夜的戈壁公路漫游,夜色吞没他们,来往的大卡车怒吼着驶过照亮他们,他们只是一直走一直走。
9.
七岁的小演员朱耕佑在生闷气,坐在剧组招待所门口的台阶上十多分钟一言不发。我坐在他旁边很小心:“说吧,佑佑。”“我不想演了。”“为什么?”他歪过头看着我:“我是佑佑,我不是乐乐(他的角色名字,我们每天都这么叫他),我也不喜欢乐乐,乐乐每天打佑佑,你不让我还手,佑佑都快被打死了。”我不由心头一震,双手扶住他小小的肩膀:“那明天就停下来休息。”佑佑露出坏笑伸出小拇指:“除非你让我每天拍完了使劲捶乐乐。”我和他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好,使劲捶。”那天以后,我们经常在拍摄前问他:“佑佑,现在可以准备当乐乐了吗?”
黄昏收工,我和佑佑走回招待所,他低着头一声不吭,很寂寞的样子。“是不是特别郁闷?”“嗯。”“知道什么是郁闷吗?”“咋不知道?就是比难过还难过。”“是不是都是大人,没有小孩陪你玩?”“嗯。”刚好是暑假,这座荒凉的小镇的街心公园经常传来孩子们嬉闹的声音。“你去那边跟他们玩一会儿,我在这儿等你,待会儿跟大家去吃一大碗你最爱的羊肉面片子。”他跑了过去。我在长椅上坐下看了几页台本,他回来了,更加垂头丧气。我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话。我们刚走到餐馆门口,他突然抬头:“小的,没意思,大的,欺负人。“我安慰他:“没事儿,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的。”他没理我,径直走进餐馆坐下来,狼吞虎咽吃起一大碗面片,好像这样就能飞快长大。
表演,完美,光线,完美,轨道,完美,录音,完美,回放检查变焦,呃,焦点跑了,各部门准备重来。我小声问佑佑:“刚才你看二勇叔叔的时候,为什么一直咽口水?”佑佑很无辜:“你说我看着二勇叔叔走了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啊?我看着看着就特想流眼泪,你还说不能流眼泪,我害怕这遍不过又重来,咽口水咽着咽着就能把眼泪咽下去了。”记忆瞬间复活,小时候自己也是这样用吞咽的办法不哭以免示弱的,忙乱之中来不及去想这个技能什么时候丧失的,甚至想不起最后一次流眼泪有多久了。
10.
太阳越来越斜,还在坚定下坠,天空中的幽蓝越来越深。现场还是一片混乱,封不住路穿帮层出不穷,群演的走位调度怎么都不准确如同乌合之众。三十多遍的“Cut!”之后,摄影指导郭达明的愤怒终于在他连续四个多月的工作中唯一一次爆发,他跳下轨道车冲我咆哮:“导演,这不公平!你不能把所有的压力都强加给摄影组!”然后转向他的兄弟们下令:“摄影组,收工!” 他独自上了他们那辆快要报废的面包车扬长而去,副导演和主任错愕地看着我,我只好低声应对:“今天收工吧。”
回驻地路上,我跟大家解释,我和达明在影视广告领域一起工作了十多年,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单纯可爱,嫉恶如仇,但从不记仇。天光本来就不接戏了,再拍下去纯属浪费,也来不及临时改拍别的场次,所以他的罢工只是一种基于周全考虑的情绪宣泄和公开投诉,而且就今天的具体情况而言,他的指责完全在理。记得新好莱坞时期的很多导演都把和摄影指导的合作关系类比成夫妻关系,我讲起了段子调节气氛,我们都认识的一位朋友的太太暴躁又顾家,他们每次激烈吵架,这位太太都会往地上砸一些本来就要扔进垃圾桶或者老旧该换的东西,即使是情绪最失控的时候,她也能把总损失控制在二十块以内。
在大家的笑声中,达明的电话来了:“到哪儿了?刚才态度不好请原谅。这场戏我有一个新的想法,咱们先讨论定了再去吃饭吧,我请。”
11.
剪辑指导今井刚先生工作室附近的小餐馆,我们吃着小菜喝着酒在等野上照代先生的到来。VCD时代看黑泽明导演的电影,几乎每一部的演职员表字幕里都有她的名字,后来看过山田洋次导演根据她的小说《致父亲的安魂曲》拍的电影《母亲》,再后来读过她的自传《等云到:与黑泽明导演在一起》,我们的后期制片人小坂史子老师是她多年的忘年交,告诉她我在东京做最终的剪辑,还去拜谒了黑泽明导演的墓地,九十岁的野上先生决定今晚放下手头的写书工作来探班。
大家忽然轰然起立,我也跟着站了起来,一位提着塑料袋的老太太背对我们在吧台跟老板说着什么,看出了我的惶恐不安,小坂姐开始小声地声情并茂模仿她:“给那桌年轻人的酒各加一份,现在付账,下酒菜我可不管。”大家都会心笑了。
野上先生在我身边坐下,一头银色卷发,穿着很优雅,她先感谢了我去看望黑泽先生,然后拿出一件印有黑泽明长孙的版画作品的T恤:“这是最后一件,你们分吧。”大家又笑了,纷纷推给了我,我毫不客气收下了,她打开那只塑料袋,向我介绍熬夜剪片分别要吃什么补充VC,营养以及提神,小坂姐提醒她我明天就定剪回国了,她立刻收起了袋子:“那我留着自己吃吧。”
野上先生问了一些《未择之路》的细节,大家起身去餐馆一角合影留念,我们在她身后要去扶她,她仿佛能红外感应,头也不回轻轻摆手婉拒了我们伸出的手。拍完照片,先生对我说:“辛苦了,加油,谢谢你。”跟大家一一欠身告别后,缓缓走出门,去坐地铁回家继续写作了。小坂姐说,她最后的谢谢是要感谢后辈为她生命中最神圣的电影事业所付出的努力。
今年夏天北京电影节的展映,去看黑泽明的《梦》,突然下起了暴雨,路上堵车迟到,进入影院看见银幕上一个男人在暴风雪中朝向我艰难跋涉,我知道我第二次看大银幕还是错过了两个半梦,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在大学小礼堂看同声传译的胶片拷贝放映也迟到了,正是从这个镜头的这个时刻开始的,想当年,我清清楚楚记得。只是这一次,在片尾看见了野上照代先生的名字,在退场的人群里,我默默起立致敬,依然惶恐不安。
(照片除图1,4,9,全部来自剧照师王宁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