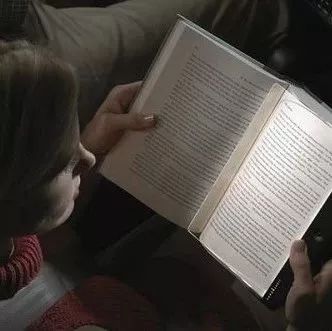正月里的洁隅年味特别浓,除了唱戏,还有一项非常喜庆热闹的活动~舞香火龙。
春舞青龙,夏舞赤龙或黄龙,秋舞白龙,冬舞黑龙知道不知道的跟我一起来进入舞龙的行列。
龙是华夏文明的图腾和符号,行云布雨,消灾降福;民间节庆,贺喜,祝福,驱邪,祭神,庙会等活动都会有舞龙的习俗。
常见的龙有布龙,草龙,香火龙,板凳龙,扁担龙等百余种。
动作分穿,腾,跃,翻,滚,戏,缠,跳,摇,扭,挥,跪,举等。
舞狮的开场是醒狮,锣声急促,震醒狮群。舞龙要请,钹声连击走场,绕场三周,龙珠出场,龙头方露。
来一场布龙,钹声走过场请龙,锣,钹,铛铛,唢吶乐器奏起,炮铳一响,伴随着喜庆的场面,龙头一摇一晃出来,气势磅礴,左耸右伏,九曲十回,时缓时急,蜿蜒翻腾,上下蹿行,时而腾起,时而腑冲,变化千万;伴着炮铳声焰火的烟雾,大有腾云驾雾的前景,锣鼓声,摇钹声,铜锣声,铛铛声,唢吶声齐奏,蔚为壮观,好不热闹,仿佛龙在云雾中飞舞一般;展示舞龙人的精,气,神,韵;展示一种民间的群众性和娱乐性;展示华厦儿女战天斗地,无往不胜的豪迈气概;渲泄着欢快的情绪和热忱。
香火龙头重不超过三公斤,以单数为节为雄龙;也有以双数为节的雌龙是妇女们舞(男女半边天后,才有母龙);本身舞龙队伍中是没有妇女的,有女性都是扮彩头举礼牌之类。
香火龙一般在夜晚进行,每舞一次一个时辰,在每节上插满点燃的香,舞完后烧掉,青烟升腾,送龙上天。
记不清是那年我跟着洁隅这条香火龙到秀流,侍客在前一天到秀流发了帖,到节妇坊时天已经黑透,各自点燃香插在龙头,龙身,龙尾上,鸣锣开道,鼓点声开始,紧接着唢吶,摇钹,铛铛一起配合着锣与鼓的节奏点,进村后,舞到哪家门口那家就点燃炮竹,一直走到祠堂门口禾坪上,全村人一起围观,香火星星点点划出道道火线,在夜空中肆意舞蹈,直舞到祠堂内才歇气。
祠堂中秀流朱氏族人早就摆上了土烧酒和托盘水果点心,还有蒸软的糍粑各种年货,来犒劳这些年青的舞龙汉子们;酒过三巡,有人预约到哪那里?年前砌了新屋要彩头;于是重新点燃香火,由龙头带路直把这条香火龙舞的天昏地暗月偏东。
回来路上我挎着的大布袋里全是糕皮,糯米锅粑,一路走一路啃得唦唦响,好象耗子嫁完女就要作姥姥似的高兴。
外公外婆俩是善良忠厚的人,有时会因一些家庭琐碎产生分歧,外公嘴笨,争不赢外婆,外公干脆从睡房中搬出来,睡到厅屋的耳房里,用两条长凳架上废门板,垫上禾草,铺张草席;外公没读过书,在他烟熏的黝黑房门后,工整地用粉笔写着“一事不管”四个字,意思是权力全权归外婆,他只管做事绝不做声,落得过耳根清净;过了些时日,又把门后的第二个字擦了改为“世”,外公老实的很有个性,总是一副笑脸。
外婆高兴时也会讲点老故事来听,讲崔氏女子与朱买臣,片断零碎,难以组合;还讲老绒婆坐在树上梳头,没头没尾;把狼外婆化装成外婆吃妹妹的故事版本改为阿婆(这个故事最早是听阿婆讲,不知道是否有两个版本);有一个故事我记得很清淅,她说是她父亲讲给她听的,是说一个女子长得有几分姿色,靠嫁人吃饭,从第一家生了小孩后,嫁东家入西家,共嫁了九十九次,再嫁一次就嫁圆满,第一百次时,她总感觉这家很熟,在天井的墙缝中发现了自己用过的断梳,才知道今晚娶自己的是亲生儿子,她羞惭难当,出家当了尼姑。
外婆经常讲她做女在娘家小时候的事,门前有株海棠开的很漂亮,盆中有勺药和昙花,她母亲绣的鞋样如何漂亮。
渡头乡是个美丽的地方,乡政府大门前是块很大的墙坊,高若十二米共两层,一边一条砖柱直冲房顶,上面实体墙成拱,拱下一个大五角星,大门四米宽成拱道,拱上凸着人民公社好的水泥字样,类似这种建筑一般是在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建造出来的。
大门的拱洞中有条老黄狗,我相信在文革至八三年内在渡头公社政府工作过的任何人都有印象,那条狗叫“冇咪”,冇咪是当地人的母言,是没有尾巴的意思,它的女主人住在我家隔壁姓张,男主人姓曹在公社上班;我听女主人讲哪条狗因小时候喜欢追家中的鸡,被主人受罚砍掉了尾巴,从此得姓名~冇咪。
冇咪在文革中不知什么事救了女主人,女主人一直很感谢它,她后来象报恩似地养着它,也难怪养过狗的人都说狗是人类的好朋友;我们家搬到那里时,冇咪已经很老了,走路时有点吃力,夏天时一身黄色的狗蠓,垂老地爬在公社门口,一天两餐回来,早上跟着男主人上班,晚上跟着男主人回家。
八三年冇咪逝世,女主人把它埋在家属区的右边食品站的山头上,面朝酸洞眼,回归大自然,永垂不朽,立墓碑作为纪念。
公社旁边那口水塘,四周一片乱象;赶集的人们主要集中在丁字路口,有次快过年在集上抓住位外地小偷,被大家打得鲜血直流后,推到塘中,水齐胸口,愤怒的群众狠心地从四周用砸头去砸,傍晚用绳索梱在法国梧桐树下;那是我第一次见人这样惩罚盗窃的人,内心里形成很大的同情心和阴影。
那年天旱,双抢插田后一个月没下雨,公社报告县里,县里用货车运来两门大炮,架在公社后面的一畦大土上,看稀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围过来,本公社有几名炮兵退武军人,穿着作训服在大炮旁边向围观的人解说怎么放大炮;渡头人讲大话吹牛皮的土语是吹大炮,看到大炮后都很惊讶,三四个人操纵,还累的满头大汗。
当天空中一朵乌云飘来,炮口抬起瞄准,指挥手举着的小红旗向下压,口哨“啹”,“嘣”的一声振聋发聩,地动山摇,待大家从炮声中醒过来再蒙耳朵时,耳鼓已经是嗡嗡着响;弹头从炮口冲出来的瞬间,火光四射,画出一条弧线直入乌云;连续放了几炮,半小时不到隔壁清江公社传来了好消息,感谢渡头公社,他们那里下雨了,下大雨了。
炮响后,附近村民水塘中的鸭子为庆祝下了雨,虔诚地向上天祭奠,献出了它们宝贵的生命,愿它们安息在人们心中的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