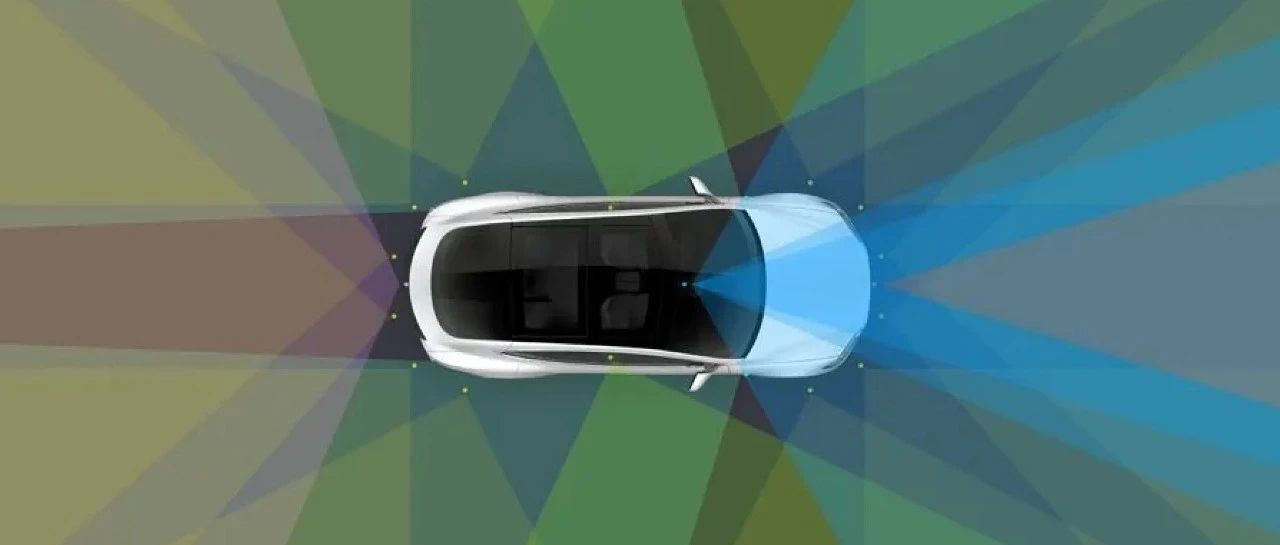原载于三联《爱乐》杂志。年过九旬的钢琴家又要来弹“平均律”第一册,他实实在在是个演奏狂。
最近几年中,德慕斯(Jorg Demus)三次来到中国演出。最初听了他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激动不已,深感德奥学派黄金年代之余辉落在眼前。原以为这样的演奏,一生听一次也便满足,未料还有后来的两场音乐会。初次访谈完成于2015年11月,钢琴家的第二次演出之后,因为关于德奥学派的某些东西,自己有疑惑萦绕于心,实在想问。竟由此冒昧地拜托了张克新先生,后者在时间条件已相当不利的情况下,促成了那次美妙的访谈。
而去年,真没料到钢琴家又来了第三回,彼时他已87岁高龄,还依旧为自己选择了分量超重的曲目。这次演出的节目册的主要内容,正是我先前那篇访谈。而我自己,也在一贯得陇望蜀的思维方式的驱使下,计划了新一次的访谈。希望能补全上次的些许遗憾,同时也更系统、更周详地规划一些问题,等等。整个过程开始得相当顺利,其间却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可由此产生的,也的确是意想不到的成果。我作为访问者,自己这么说也不觉得惭愧。
张可驹(以下简称“张”):很荣幸再次采访您。您从很早就开始研究早期钢琴,并且不同时代的钢琴作品也都采用过本真乐器来录音。您曾经说过,羽管键琴因为机械结构的关系,其实并不适合用来表现巴赫。而对于早期钢琴,并不在意类似的问题吗?这些乐器对您演奏有何启发呢?
德慕斯(以下简称“德”):这要从早前的那些乐器说起。羽管键琴和管风琴由于它们本身的结构的关系,其实不太适合声音上的塑造。因为每个音之间,并不能真正地连在一起,音色也缺乏变化,太相似了。卡萨尔斯曾在东京的一次晚餐上对我说:每个音都不要太相似,不能是“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这种状态。演奏巴赫需要如此,弹莫扎特的奏鸣曲也不无二致。(钢琴家哼出一段旋律)音色要有变化,就像德语的发音那样,不是单纯的说话,而是带点朗诵般的语调。
张:您既用现代钢琴来弹莫扎特,也用本真乐器演奏,请问后者对您理解作品有怎样的帮助?
德:我想接近莫扎特先生,越接近越好。但这种“接近”,并不是设法触摸他的头发或牙齿,或他逝后的面膜,而是去接近他所使用的乐器。当年,那些擅长演奏钢琴的作曲家们都有自己钟爱的乐器,我就是要去研究这些乐器。莫扎特喜欢安东·瓦尔特的钢琴,贝多芬喜欢布洛伍德,而舒曼就喜欢格拉夫的钢琴。当我演奏这些乐器的时候,就能够去接近莫扎特,去接近贝多芬了。
张:您重要的合作者巴杜拉—斯柯达曾表示,如果巴赫或莫扎特看到现代钢琴,恐怕未必会赞叹其性能,而是感到这个像棺材一样庞大的乐器声音太大,又太浑浊。请问您对此怎么看呢?
德:你为什么提到他的看法?
张:因为你们都是对早期钢琴最有研究的钢琴家。很多钢琴家都认为,倘若巴赫、莫扎特看到今天的乐器,便会欣然接受,巴杜拉—斯柯达却完全不认同。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德:这我怎么能知道呢?How do I know?
张:在莫扎特的年代,钢琴和乐队的音量都与今日不同,二者的分量、比例您认为如何表现比较好?
德:还是要从当代的、今天的角度出发,就像我们没有必要想着回到从前的萨尔斯堡,去吃莫扎特当时的某道菜。贝多芬当年用双腿走路,我也是,可我现在腿脚不好,所以就坐汽车。这是今日的便利,当然没必要拒绝。我虽然研究本真乐器,却并不是历史学者型的演奏家,我是一位音乐家。
张:很少有钢琴独奏家像您这么热爱艺术歌曲。
德:那是因为其他的钢琴家都很笨。当罗伯特·舒曼创作他的艺术歌曲时,他写下了极美的钢琴部分,也接受克拉拉的意见。我很高兴,自己弹得足够好,能够去演奏他们创作的歌曲,弹那些被称为伴奏的钢琴部分。但不幸的是,我愿意为之伴奏的歌唱家们都已经不在了。所以,现在人们说我脾气不好,因为我对他们喊叫。如果那些歌唱家不够强大的话,他们就会被我的喊叫所击垮。
张:我特别想请您谈谈莫扎特的艺术歌曲。有些独奏家还愿意弹舒伯特、舒曼的歌曲,可是对莫扎特问津都不多。您却将他的歌曲录了多次。
德:没有“莫扎特的艺术歌曲”,不存在这种东西,莫扎特只写过咏叹调。
张:没……没有?那么您和阿美琳、彼得·施莱尔这些人合作灌录的又是什么呢?
德:莫扎特只写过咏叹调,歌剧咏叹调,音乐会咏叹调这些。贝多芬创作了第一首艺术歌曲Lieder。
张:可您录过莫扎特和海顿的唱片。
德:是贝多芬创作了第一首艺术歌曲,海顿写的只是一些英文的歌曲,还有一些很小的“歌”。而“艺术歌曲”这种东西,其实是一位作曲家和他自己说话。(唱出贝多芬的《我爱你》WoO 123)贝多芬这样的歌曲就是在和自己说话。(唱出舒伯特的《致音乐》)舒伯特也是这样,和自己说话。莫扎特却不然,在他的“歌曲”中,他并不是和自己说话,而是推出一个歌剧人物。就像他笔下的塔米诺、艾尔薇拉这样,由他们来说话,莫扎特的歌曲中都是有角色的。
张:我第一次听到这么精辟的见解!
德:那些歌唱家灌录了“莫扎特Lieder”的唱片,但其实那个“Lieder”是后人写的,而并不是莫扎特自己写的。
张:人们说舒伯特改变了艺术歌曲的历史,您能谈谈这个问题吗?
德:这么说是不对的。因为艺术歌曲其实是贝多芬创造的,而贝多芬和舒伯特又是同时代人,甚至他们去世都相隔不久。贝多芬在1827年去世,而舒伯特是1828年。舒伯特崇拜贝多芬,并向他学习。只是贝多芬有很多其它的事情要做,要写他的交响曲、协奏曲、四重奏等等,所以他没有创作那么多的艺术歌曲。舒伯特写了七个Volume的歌曲,而贝多芬只写了一个。德国的艺术歌曲确实是从贝多芬开始的。
张:您曾经提到,要表现舒伯特的器乐作品,也必须了解他的歌曲。而他的《美丽的磨坊女》与《冬之旅》这两部声乐套曲,都是非常悲剧性的作品,《冬之旅》的结尾更是无以复加。
德:那两部连篇歌曲都以悲剧结束的说法也是不对的。
张:Why?
德:当《冬之旅》最后的旋律出现时,那个年轻人离开了。可在那之后,他很可能又活了五十年!《美丽的磨坊女》是真正的悲剧,因为最后主人公跳河自杀了。可《冬之旅》并不是悲剧结尾。这显然是那个人生命中极为悲伤的时刻,但之后,他还会爱上别的女孩。你过去曾经不快乐,但你现在已经幸福了。我也有悲伤的时刻,但我没有自杀,因为我不是悲剧的性格。不过,你为什么一直问这些同音乐史有关的问题呢?
张:因为能像您这样谈论这些问题的人,如今已经凤毛麟角了,所以我才问您。
德:巴杜拉—斯科达对于很多历史性的东西比我更了解,但我比他更有音乐性,哈哈。布伦德尔也是,他“脑中”有很多东西,“心里”却没那么多。可是,倘若缺少了“心”,缺少了“品位”,缺少了“灵魂”,都是无法理解那些伟大作品的。所以,你认为我今天所说最重要的话是什么呢?
张:就是您刚才的总结吗?我会铭记于心的。
德:不,是卡萨尔斯对我说的那一句:永远不能演奏雷同的音。当一个人枯燥地演奏时,是这样的(钢琴家唱出枯燥感十足的旋律),每个音都很准确,却忽视了它们彼此之间的“连接”。但一个人如此演奏,也不会用这种状态来说话。好的音乐就是语言,同语言之间的关系很大。可是中国人似乎并不是很努力地去学其他国家的语言,日本也是如此。有一次,我在日本的一个火车站里走进一家书店,里面没有一本英文书,也没有一份英文报纸。哪怕就办公来说,没有英语又怎么办公呢?学习语言,学习音乐的语言是最重要的事情。
张:您有一款录音我特别着迷,就是您同费舍尔—迪斯考合作,为DG灌录舒曼的《诗人之恋》,您能谈谈那次合作吗?
德:有两次录音,一次是单声道,费舍尔—迪斯考30岁时录的,另一次是立体声,当时他45岁。你听的是哪一次?
张:是立体声的那一次。
德:你要我谈那次录音,而我要反问你,你认为《诗人之恋》中的主人公,他应该是多大年纪?
张:我不知道,肯定不算大,但也不太幼稚,因为他处理失恋的态度同舒伯特笔下的……
德:你到底认为他年纪多大!?当他唱出这样旋律(钢琴家唱出《诗人之恋》的开头)。
张:25岁左右?
德:没有那么大,也许只有19岁。这样一个人在讲述他的恋爱。费舍尔—迪斯考第一次录音时年纪和他更接近,所以是第一次录音比较好,更接近那个人物。
张:也许,人看待恋爱的心态和年龄没有必然联系?
德:这么说不过是纸上谈兵。完全和年龄有关,关系非常、非常大。当你成熟的时候,你在爱中给予的东西更多,而当你19岁时,并不是那种完全精神层面的爱。这样,当他唱出“我曾深深爱过玫瑰、百合、鸽子与阳光,但现在……”(《诗人之恋》第3曲的开头),这并非完全的精神层面的爱,而是全身心地投入,浸透在其中,这个年轻人在唱他最好的爱(the best)。
张:能否谈谈您在Westminster的录音?现在它们很有影响,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多人热爱这些唱片。那是个特殊的年代?
德:哦,是的,是的,那是我最初的录音。维也纳有很好的音乐厅,而战后,年轻一代的音乐家出现了。新一代的钢琴家,巴杜拉—斯科达、我,海布勒、瓦尔特·克林,这些人登上舞台,都想要演奏,还有布伦德尔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很多唱片公司都来到维也纳进行录音,那里又有两个美妙的音乐厅,金色大厅和维也纳演奏厅。他们自然乐意在那里录了。而这些钢琴家,他们也成为第一批灌录LP唱片的人。我和LP的关系尤为紧密,因为LP是1948年发明的,而我是在1949年首次录音。伴随这个过程,维也纳也从战争的摧毁中真正复活,Westminster的录音就是记录了这样一个时代。正是在这个时候,唱片公司邀请我和巴杜拉—斯柯达灌录了大量的莫扎特,还有众多舒伯特,我们就是从那时开始合作的。
张:能谈谈您和维也纳爱乐首席们合作灌录的室内乐吗?
德:那是一个很短的时期,因为维也纳爱乐的那些首席们……哈,他们都很骄傲,就是这样。有一段时间维也纳爱乐和古尔达录音,但后来也对他失去了兴趣,之后他们和布伦德尔录唱片,这是由于唱片公司付了很多钱。在音乐会的现场,我和维也纳爱乐只合作过一次。卡拉扬指挥乐队演出巴赫的《第五号勃兰登堡协奏曲》,原定采用羽管键琴,但是卡拉扬不愿意。他想在键盘乐器的部分采用钢琴,并执意邀请我来弹,这是唯一的一次。单单演出乐队作品让维也纳爱乐的乐手们有些疲倦了,于是他们就组成一些相当迷人的室内乐组合。譬如维也纳演奏家合奏团,各样的几重奏,那些重要的四重奏,像演奏厅四重奏、巴雷利四重奏等。
张:您早前在Westminster录音,后来又在很多公司灌录唱片。请问在这样的过程中,您看到了怎样的变化?
德:在Westminster的时候很愉快,录音的速度也快。大家的演奏充满自发性,其实有时演奏得不好,也无所谓,也就过了,但所幸我演奏得还不错。而在DG那边,录制一张唱片的时间要长很多。Westminster时期,经常是两天录完,有时甚至就是一天完成。而在DG,往往需要一周的时间。Westminster的做法也不错,可DG在技术的细节上关注更深。当然音乐方面都是由我们来提供了。当时巴杜拉—斯柯达与奥伊斯特拉赫合作灌录了莫扎特的奏鸣曲,那些唱片也非常精彩。(注:这套唱片不是为DG录的,钢琴家应该是回顾大致一个阶段的录音)
张:可是很多人不喜欢奥伊斯特拉赫的莫扎特。
德:我不管很多人怎么想,我只是自己买一张唱片来听,看看究竟喜欢不喜欢?我从来不管很多人怎么想。如果我在意很多人的意见,我可能很早之前就自杀了。很多人都说勋伯格、韦伯恩的音乐了不起,但我觉得它们真的很恐怖。
张:那您很喜欢奥伊斯特拉赫的莫扎特吗?
德:其实我喜欢巴杜拉—斯科达的部分更多些。奥伊斯特拉赫在音乐会上有很多精彩的演出,那些协奏曲,勃拉姆斯那首,西贝柳斯的协奏曲甚至更好。但表现莫扎特,某些句子需要处理得特别清晰,而奥斯意特拉赫的演奏就比较浪漫。所以我还是更喜欢维也纳人演奏的莫扎特,当然他们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肯定比不上他。不过那些录音还是很好的,录完后,奥伊斯特拉赫也很高兴。
张:一份唱片说明书中写到,您跟随埃德温·费舍尔学习,同富特文格勒、卡拉扬合作演出。他们都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音乐家,您能够谈谈他们吗?
德:事实上我没有和富特文格勒合作过。原本有计划,在1954年,他把他自己创作的《钢琴协奏曲》的乐谱给我,让我学了之后准备合作演出。但可惜,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我失去了同他合作的机会。我非常崇拜他,却没能和他一起演奏。而卡拉扬,我与他合作了12次,曲目包括莫扎特《为三架钢琴而作的协奏曲》,还有他最后的钢琴协奏曲K.595,这首我们合作了多次。当然也包括之前提到的《第五号勃兰登堡协奏曲》。我们在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和维也纳都合作过,还有卢塞恩,当然还有柏林。你不好奇为什么我们会合作这么多次吗?
张:可是,这也很正常啊,您弹得这么好,而卡拉扬也是有品位的。
德:不,不尽然,真正的原因是我感到自己同卡拉扬之间有某种“化学反应”。同施瓦茨科普芙合作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反应。就是合作的双方都不用去改变自己原本的诠释,彼此却又能很好地合到一起。这是好的音乐家之间的那种“感应”。和阿美琳之间也一样,很快就出现了这样的好感。
张:您和阿美琳灌录的莫扎特歌曲,无论这些“歌曲”该叫什么,我真的太喜欢那张唱片了。
德:不过我们合作舒伯特、舒曼的歌曲还是更好一些。你既然喜欢莫扎特的录音,就应该找那些艺术歌曲来听。
张:您刚才提到,富特文格勒曾把他的协奏曲给您,我很好奇您怎么看待他的作品?您自己也是一位作曲家,和富特文格勒一样,而你们的创作风格在今天看来是相当保守的。
德:相对于那首协奏曲,我还是更喜欢他的《第二交响曲》,那是富特文格勒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首。他的小提琴奏鸣曲,《钢琴协奏曲》和《第三交响曲》,这些作品我都了解。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第二交响曲》。他自己指挥柏林爱乐灌录的那张唱片,你应该找来听听。不过,富特文格勒身为作曲家,可说是处在一个(创作)流派纷呈的时代。有调性,无调性等等,当时都在激烈的碰撞。他指挥了勋伯格为柏林爱乐所作的变奏曲的首演。后来希特勒来了,将现代音乐定义为可怕的作品,所以富特文格勒也不能再去触及。而我自己创作音乐,是从战争结束之后,最初是1946年。之前也写过,但真正开始创作是从1946年,所以我对音乐风格的取舍同希特勒来不来完全没有关系。只是在我自己的品味中,进行自由的选择,而我自己的品味也就体现在我的作品当中了。这次来上海,我也要在音乐会上弹我自己创作的奏鸣曲。也许你对这样的作品不感兴趣。可你究竟怎么看呢?
张:哦不,事实上我很感兴趣。我之前不仅听过您的作品,这次还带了唱片来请您签名留念。富特文格勒的作品很感动我,您的作品也一样。尽管您在唱片说明书中写到,可别将它们与贝多芬的大作相比,但是在今天,您依旧敢于采用这么传统的风格来创作,仅这一点,已经让我无比钦佩。在20世纪,还有人写如此动听的音乐!
德:其实无所谓“传统的风格”,我只是依照调性音乐应该是什么样子来写。如果说,我是“依照贝多芬时代的风格来创作”,那是不对的。和声等等,我都只是采用一种最自然的调性音乐的语言来创作。贝多芬也是用这些自然的音乐语言来写,勃拉姆斯也是,而到德彪西之后,基本上就结束了。我要回到那些伟大的音乐家的年代,向他们学习,而不是去模仿他们。所以,要创作有调性的音乐,你这篇访谈就以此为标题吧,就写《要创作有调性的音乐》。
张:好的。最后的问题是关于贝多芬的音乐。您曾写过关于贝多芬奏鸣曲演绎的书,新近发行的两张唱片中,也分别收入两首晚期奏鸣曲(Op.109与110)。演奏这些作品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德:我只写了半本,那是同巴杜拉—斯科达合著的,32首奏鸣曲中,每人写16首。要说演奏它们对我意味着什么,哈哈,那么蓝天对你意味着什么呢?太阳、月亮、水这些对你又意味着什么呢?贝多芬的奏鸣曲每一首都不同,有些真是伟大得无以复加,没有人曾经触及那样的境界。其中Op.111是最巅峰的,而Op.49中的小奏鸣曲,对他来说,也带有一些娱乐的东西。这些奏鸣曲就像是天空一样,天空既覆盖着上海,也覆盖着萨尔斯堡。你不妨具体到某一首奏鸣曲。
张:我特别想问的就是最后的奏鸣曲Op.111,如此伟大的作品,它和贝多芬先前写的那些二乐章奏鸣曲之间有关系吗?
德:不,没有关系,它们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关联。贝多芬先前的二乐章奏鸣曲基本都是“小奏鸣曲”,可是Op.111的两个乐章,就如同将两个世界摆在你面前。第一乐章(钢琴家唱出乐章的主题),它仿佛代表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而第二乐章,代表了天堂的永恒。这首和之前那些作品没有关联,只有音乐学家认为它们有关。
张:您会将最后三首奏鸣曲看成一体吗?
德:我认为是的。因为贝多芬年轻时,经常将三首奏鸣曲放在一个作品号里,Op.2 No.1、No.2、No.3这样,Op.10与Op.31两套作品也都是如此。最后三首奏鸣曲也许可以称为Op.109的第一、二、三号,但由于它们彼此之间有极大的差别,每一首又都太重要,所以还是不能这么放。
张:非常感谢您接受访问。并且,我还要向您致以“个人的”、访谈之外的感谢。因为,其实我正是通过您的唱片,第一次真正爱上贝多芬的作品,是您与加尼格罗合作的五首大提琴奏鸣曲。
德:加尼格罗实在、实在是一位非凡的大提琴家。不过,完成那套录音的时候他已经离开巅峰状态了,尽管还是拉得很好。因为之前他遭遇到严重的事故,腿和腰都摔断了。哪怕在伤愈之后,他演奏时也会感到种种不适。所以那套录音完成以后,我们也没有机会再合作演出了。但唱片本身还是很不错的。
以下是这次访谈的一小段后记:
因为机会难得,之前又有一些时间准备,所以相对于前一次,一挥而就的访谈提纲,本次对于提问的内容作了更加全面的设计。然而在具体操作中,我也只能奋力“见风使舵”,以避礁石。所幸有张克新先生在,他既是最好的翻译,又即刻为我指点迷津,因此需致以两重的谢意。同时,也感谢起初帮我联络的李向荣兄。我始终期待他们所安排的演出。
之所以从本真乐器的问题开始,除了因为德慕斯是这方面的专家之外,很多也是对于德奥学派一些更深层的好奇。焦元溥曾在《游艺黑白》中比较俄国钢琴学派与法国学派、德奥学派之间的差别,认为俄国学派对于莫扎特的隔膜,有很多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是从19世纪中后期,渐渐走向成熟的大钢琴的性能中建立起来的。而德奥学派,以及法派的钢琴演奏,则是从羽管键琴一路发展到海顿、莫扎特所使用的木结构的早期钢琴。因此他们表现莫扎特音乐更为得心应手。
我并不是认为他的观点一定是对的,可毕竟,德奥学派与法派钢琴家在表现古典作品时,音响构思方面的相似仍是比较明显的。就以莫扎特为例,欣赏施耐贝尔、肯普夫,或是蕾菲布、卡萨德絮的演奏,多少会发现他们对于“古典风格”的认识有共通之处,即便他们的“莫扎特观”可能完全不同。而在俄系的演奏中,甚少出现这种共通之感,在一些俄系思维主导的超技风演奏中亦然。
因此我很希望德慕斯能够谈一下本真乐器。因为系统性地研究早期钢琴,他和巴杜拉—斯柯达毕竟是德奥学派真正的先驱。先前的钢琴家们也会关心,但可能没有这么系统。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吉塞金表示,他发现莫扎特的钢琴是没有踏板的,所以在现代钢琴上演奏莫扎特,也应当尽量不用踏板。谈到这件事,巴杜拉—斯柯达半开玩笑地说:这是因为吉塞金的身材太高大了,如果他蹲下来看一看,就会发现今天的“踏板装置”,在当时是用膝盖来操作的。而到了他和德慕斯的这一代,不仅本真演奏蓬勃发展,他们也成为研究早期钢琴的主力。
然而,相对于巴杜拉—斯科达那种对于早期钢琴的痴迷(譬如换三架琴,灌录舒伯特D.960),德慕斯以现代钢琴为根本,汲取本真,而后兼容本真的思维在他的录音中也表现得很充分。正如钢琴家在访谈中所说,研究本真乐器是他接近作曲家的方式,可最终的音乐表现,很多仍需要从当代的、今天的角度出发。这也就是为何听德慕斯演奏莫扎特时,我们从来不会感到他将乐器束缚在某种本真的格局之内。钢琴家会直接用本真乐器录音,可一旦他选择了现代钢琴,对于这件乐器的音响特点的发挥,有时会惊人的大胆。但结果,又往往是树立了“现代钢琴上表现莫扎特风格”的典范。与之相对,前述巴杜拉—斯柯达与奥伊斯特拉赫合作莫扎特的录音中,钢琴家采用现代乐器描摹本真的构思,几乎强烈得无以复加。他未必一直会这么弹,但此时,那样的倾向很明显。
古老的作曲家面对现代钢琴时可能出现的观点,这一向是钢琴家们众说纷纭的话题,而像德慕斯这样,直截了当地回答:“How do I know?”或许也是值得我们记住的。事实上相对于乐器,钢琴家反复强调的一点其实是语言。“好的音乐就是语言,同语言之间的关系很大。”前一次访谈中,他已经提到卡萨尔斯的观点,可当时我的确没有意识到,那对于钢琴家来说有怎样一种提纲挈领的“指导意义”。不同的音,各自的变化、区分,彼此之间的连接,被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至于钢琴家提到,中国人似乎并不热衷于学习语言这件事,这势必是他的误解。事实上,目前国人对外语的热衷已到了不正常的地步。但他碰巧遇上了我,考虑到翻译占用时间,这些细枝末节也无从解释了。假若外语人才没有来进行此类的访谈,大概是因为他们在忙别的事情罢。
哪怕在音乐之外,访谈中也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从来不管很多人怎么想。如果我在意很多人的意见,我可能很早之前就自杀了。”诸如此类。至于钢琴家提到,他会对歌唱家们“喊叫”,想必是确有其事,因为我碰巧也遇到了几次。所幸没有全垮,而这也就是你读到这次访谈的原因。